谁都有过一段特别没有底气的日子。
室友到宿舍门外了,正在掏钥匙。
“还有五秒钟给我写完这一句,还有四秒,三秒,快好了!”
宿舍里的 Acher ,在心里一边这样盘算着,一边用最快的手速敲打键盘,尽全力赶在室友看到他的电脑屏幕之前,完成正在撰写的小说章节。
终于在宿舍门“嘭”地一声被打开的那刻,他及时地在章节的最后一句上落下了句号,然后娴熟地操作着 Alt + Tab ,把电脑界面切换到英雄联盟的游戏界面。
“在打游戏啊。”室友经过他身后说。
“是啊。” Acher 如释重负。
在两年半前,这样的生活情节,每天都会在尚是大四学生的 Acher 的生活中上演。
也不是没有失算的时候。
好几次因为各种状况, Acher 还是会被室友看见他在 word 文档上写下的密密麻麻的文字。
没有细看的内容的室友通常就会说:“论文不用这么快开始写啦,你真的也太勤奋了吧。”
或者是:“你是在写自己的书吗?好厉害。”
听到这样的话,Acher 通常只能硬挤出一个标准的笑容,然后吐出一句没有灵魂的“没有啦”。
会被误解也可以理解。
大学前三年,Acher 都活跃于学生会,学生会会长的经历,让他有充足的存在感和成就感。
“他们总是觉得我应该是在做很厉害的事,尽管我只是在写一些无聊的故事。
所以每次听到他们这些话时,我就觉得很累,很没有底气。”回忆起来,他的语气还是满带无奈。
大三的最后两个月,Acher 即将卸任学生会会长,他开始意识到,自己很快就变回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普通人。
再也找不到成就感的来源,Acher 的内心变成了一个悬在半空的氢气球,轻飘飘的,变得很虚。
在六个人的宿舍里,他一直觉得自己是最黯淡的存在。
读师范的室友都下乡支教了,读戏剧影视的同学去到了很远的一个地方正在拍摄自己的电影,当电影拍摄完成后,这个同学的名字将会方方正正地出现在字幕里“导演”的名衔底下。
即使是看起来最无所事事的那位室友,每个月也有来自几套租房的房租收入,就算每天躺着也衣食无忧。
我明白那样的感觉。这样的生活,就像万年青年旅馆的一句歌词,“前已无通路,后不见归途。”
在 Acher 的书桌上,贴着一句简单的话,是大一入学时准备的。
“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”
到了大四,他才第一次觉得,这句话原来可以这么扎眼。
“我的光,是不是已经发完了?”
他想不明白,为什么大学活得这么用力,还是没办法找到自己的底气。
这种感觉,让他觉得很煎熬。
读师范的室友都下乡支教了,读戏剧影视的同学去到了很远的一个地方正在拍摄自己的电影,当电影拍摄完成后,这个同学的名字将会方方正正地出现在字幕里“导演”的名衔底下。
即使是看起来最无所事事的那位室友,每个月也有来自几套租房的房租收入,就算每天躺着也衣食无忧。
我明白那样的感觉。这样的生活,就像万年青年旅馆的一句歌词,“前已无通路,后不见归途。”
在 Acher 的书桌上,贴着一句简单的话,是大一入学时准备的。
“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”
到了大四,他才第一次觉得,这句话原来可以这么扎眼。
“我的光,是不是已经发完了?”
他想不明白,为什么大学活得这么用力,还是没办法找到自己的底气。
这种感觉,让他觉得很煎熬。
当 Acher 对着“是金子总会发光的”惆怅地叹出一口气时,在他的正北方,Henry 正在徒步穿越滇藏线。
穿越滇藏线,是 Henry 的实验。
他从小到大都在做一个“他们是不是在乎我”的实验。
10 岁的时候,他就发现,自己并不是父母亲生的。
“这件事造成我,从小到大,都活得挺没底气的。”
时到如今,Henry 的爸妈依然没有向他坦白,而 Henry 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。
关于这个话题,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微妙的心照不宣。
“我从哪里来”这个困扰着全人类的终极命题,在 Henry 面前显得特别具体可感。
他时常因为自己没有来处,而与这个世界有着强烈的割裂感。
“我走在路上,都觉得自己的步子是踏不了在地上的。”他这么形容。
他不敢谈论未来,不敢谈论理想,甚至不敢谈论爱与被爱。
而他最为惧怕的,是谈论亲情。
每次父亲节和母亲节,他都会给爸妈发短信。
但是,事实上每一次发送短信,他都要经历一次忐忑和挣扎。Henry 有时候会觉得,自己敲下“爸爸 / 妈妈节日快乐”这几个字时,就像是一个机器人,在完成一道没有意义的工序。
而更让他煎熬的是,每一次发送完之后他都会急切地守着手机,等待着爸妈回复的一句“谢谢儿子”。
因为,他需要末尾的“儿子”两个字,来确定自己在他们心里的角色。
在 Henry 23 年的人生里,这样的“确定”他变着花样地干了无数次。
比如故意逃学让父母急到抱着他哭,比如假装自闭让父母没日没夜地守在身边。
比如这一次,未经允许就跑到滇藏线去。
“从头到尾,我都不会主动给他们打一个电话。
而每一次接到他们的电话时,我就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”
穿越滇藏线,是 Henry 的实验。
他从小到大都在做一个“他们是不是在乎我”的实验。
10 岁的时候,他就发现,自己并不是父母亲生的。
“这件事造成我,从小到大,都活得挺没底气的。”
时到如今,Henry 的爸妈依然没有向他坦白,而 Henry 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。
关于这个话题,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微妙的心照不宣。
“我从哪里来”这个困扰着全人类的终极命题,在 Henry 面前显得特别具体可感。
他时常因为自己没有来处,而与这个世界有着强烈的割裂感。
“我走在路上,都觉得自己的步子是踏不了在地上的。”他这么形容。
他不敢谈论未来,不敢谈论理想,甚至不敢谈论爱与被爱。
而他最为惧怕的,是谈论亲情。
每次父亲节和母亲节,他都会给爸妈发短信。
但是,事实上每一次发送短信,他都要经历一次忐忑和挣扎。Henry 有时候会觉得,自己敲下“爸爸 / 妈妈节日快乐”这几个字时,就像是一个机器人,在完成一道没有意义的工序。
而更让他煎熬的是,每一次发送完之后他都会急切地守着手机,等待着爸妈回复的一句“谢谢儿子”。
因为,他需要末尾的“儿子”两个字,来确定自己在他们心里的角色。
在 Henry 23 年的人生里,这样的“确定”他变着花样地干了无数次。
比如故意逃学让父母急到抱着他哭,比如假装自闭让父母没日没夜地守在身边。
比如这一次,未经允许就跑到滇藏线去。
“从头到尾,我都不会主动给他们打一个电话。
而每一次接到他们的电话时,我就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”
从 Henry 成功穿越滇藏线数起的整整两年后,有一个男生在飞行员招生报名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这个男生是我。
那天早上,在七个闹钟响过后,我艰难地从宿舍的床上起来,睡眼惺忪地被室友拖着去到了学校春招的摊位。
大四了,这是我头一回给自己设了七个闹钟。
当然,也是头一回逛学校的春招。
那段时间,我过得颇为煎熬。
我刚从一家当代艺术馆里辞了职,回到了学校着手撰写毕业论文。
也是那个时候,我要为即将到来的清考做准备,如果考不过去,我就毕不了业。
同样是那个时候,我被拉进了学院的毕业生微信群。群上反复刷着各种招聘信息,而这些职位,没有一个是我想要做的工作。
我越来越害怕,越来越怀疑。
我甚至有些开始相信,我在未来会走进一段我并不喜欢的生活里。
这个男生是我。
那天早上,在七个闹钟响过后,我艰难地从宿舍的床上起来,睡眼惺忪地被室友拖着去到了学校春招的摊位。
大四了,这是我头一回给自己设了七个闹钟。
当然,也是头一回逛学校的春招。
那段时间,我过得颇为煎熬。
我刚从一家当代艺术馆里辞了职,回到了学校着手撰写毕业论文。
也是那个时候,我要为即将到来的清考做准备,如果考不过去,我就毕不了业。
同样是那个时候,我被拉进了学院的毕业生微信群。群上反复刷着各种招聘信息,而这些职位,没有一个是我想要做的工作。
我越来越害怕,越来越怀疑。
我甚至有些开始相信,我在未来会走进一段我并不喜欢的生活里。
更重要的是,那个时候,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。
她是一个画家,已经在全国各地办过好几场画展。
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,我们因为一些原因断了联系。而在失去联系的那段时间,我好像找不到任何底气去重新找回她。
看起来是默契地在她的生活里退场,事实上更像是我怯生生地知难而退。
我还记得,有一次我在学校简陋的生活区里吃着 15 块一大碗的牛肉丸汤饭,手机里收到了妈妈在我没有收入时就会定期转给我的 2000 块。
这 2000 块,是我接下来一个月的预算。
“谢天谢地,裤头又可以松一些了。”我想。
而五分钟后,我收到了那个女生发来的微信。
她告诉我,她又以四万块的价格卖出了一幅画。
“哇,恭喜啊!”我回复了她,然后又喝了一口牛肉丸汤。
我仿佛看见了我们一起攀登一座高山,她早早地到了半山腰,回过头来对我笑。
她笑得很美,我想跟上她,却发现眼前的路被浓密的杂草层层掩盖,好像每向前一步都是一个泥潭。
所以,当她又继续向更远处走的时候,我根本说服不了自己喊出一句让她留下的话。
因为,我连自己的路在哪都没有看清。
我只好在她已经消失了的路径上,耐心地把眼前的杂草拔掉,好让自己看见一个方向。
于是,我报考了飞行员。这是在我人生规划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份职业,我报考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,
“看,我终于有一个方向了。”
她是一个画家,已经在全国各地办过好几场画展。
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,我们因为一些原因断了联系。而在失去联系的那段时间,我好像找不到任何底气去重新找回她。
看起来是默契地在她的生活里退场,事实上更像是我怯生生地知难而退。
我还记得,有一次我在学校简陋的生活区里吃着 15 块一大碗的牛肉丸汤饭,手机里收到了妈妈在我没有收入时就会定期转给我的 2000 块。
这 2000 块,是我接下来一个月的预算。
“谢天谢地,裤头又可以松一些了。”我想。
而五分钟后,我收到了那个女生发来的微信。
她告诉我,她又以四万块的价格卖出了一幅画。
“哇,恭喜啊!”我回复了她,然后又喝了一口牛肉丸汤。
我仿佛看见了我们一起攀登一座高山,她早早地到了半山腰,回过头来对我笑。
她笑得很美,我想跟上她,却发现眼前的路被浓密的杂草层层掩盖,好像每向前一步都是一个泥潭。
所以,当她又继续向更远处走的时候,我根本说服不了自己喊出一句让她留下的话。
因为,我连自己的路在哪都没有看清。
我只好在她已经消失了的路径上,耐心地把眼前的杂草拔掉,好让自己看见一个方向。
于是,我报考了飞行员。这是在我人生规划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份职业,我报考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,
“看,我终于有一个方向了。”
这是三个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年轻人,在各自的人生中经历的三段没有底气的日子。
你可能会留意到,在三个故事里,都有“煎熬”这个词。
每个人都会有特别没有底气的时候,而在这些时候,我们也通常免不了倍感煎熬。
但是,我们这三个没有底气的年轻人走到现在,变成什么样了呢?
Acher 和我说,奇妙的是,在那段看不见明天的日子里,他写下的数十篇“无聊小说”,给了他许多在日后的工作中用得上的奇思妙想和写作素材。
这让他在如今的职业生涯里,多了一份他此前未曾预设过的底气。
Henry 呢,在采访的末尾,他告诉我,有一个晚上他躺卧在林芝郊外的一片草地上,和父母通话。
他听见,爸爸妈妈在那头哭了。他们一边哭,一边颤抖着说:
“你要注意安全,无论你做什么,爸妈都是支持你的。”
这句话没有“儿子”这个词,却让 Henry 的泪腺决了堤。
林芝的天空霎时间在 Henry 眼前模糊成一片,那一刻他感觉,他终于和这个世界连在了一起。
“那是我做过的最疯狂的事,而他们却都毫无条件地支持我。
那一刻我觉得,去他妈的血缘关系,他们就是我的爸妈,我最坚强的后盾。”
你可能会留意到,在三个故事里,都有“煎熬”这个词。
每个人都会有特别没有底气的时候,而在这些时候,我们也通常免不了倍感煎熬。
但是,我们这三个没有底气的年轻人走到现在,变成什么样了呢?
Acher 和我说,奇妙的是,在那段看不见明天的日子里,他写下的数十篇“无聊小说”,给了他许多在日后的工作中用得上的奇思妙想和写作素材。
这让他在如今的职业生涯里,多了一份他此前未曾预设过的底气。
Henry 呢,在采访的末尾,他告诉我,有一个晚上他躺卧在林芝郊外的一片草地上,和父母通话。
他听见,爸爸妈妈在那头哭了。他们一边哭,一边颤抖着说:
“你要注意安全,无论你做什么,爸妈都是支持你的。”
这句话没有“儿子”这个词,却让 Henry 的泪腺决了堤。
林芝的天空霎时间在 Henry 眼前模糊成一片,那一刻他感觉,他终于和这个世界连在了一起。
“那是我做过的最疯狂的事,而他们却都毫无条件地支持我。
那一刻我觉得,去他妈的血缘关系,他们就是我的爸妈,我最坚强的后盾。”
而我呢?
毕业后,我只身前往北京,又辗转了上海,参加了一个月的飞行员培训,以及几次航空公司的面试。
尽管没有继续在飞行员这条路上坚持下去,但是这段经历也让我更认清自己,原来是可以有从前没有想过的毅力和勇气的。
这些美好的自我认知,对我接下来人生中的每一步路,都将会是意义重大的。
而我也终于又找到了那个女生。
我对她说,虽然我没有想过能再和她重逢,但事实上,在潜意识里,我去年做的每一个决定,都会先思考这样做,能不能更靠近她一些。
没想到,这句话成为了我说过的话里,最让她心动的一句。
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是,当我们感到自己没有底气的时候,也正意味着我们将要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了呢?
如果是这样的话,你也正在为自己活得特别没有底气而烦恼吗?恭喜你呀,再坚持一下吧,
就一下。
毕业后,我只身前往北京,又辗转了上海,参加了一个月的飞行员培训,以及几次航空公司的面试。
尽管没有继续在飞行员这条路上坚持下去,但是这段经历也让我更认清自己,原来是可以有从前没有想过的毅力和勇气的。
这些美好的自我认知,对我接下来人生中的每一步路,都将会是意义重大的。
而我也终于又找到了那个女生。
我对她说,虽然我没有想过能再和她重逢,但事实上,在潜意识里,我去年做的每一个决定,都会先思考这样做,能不能更靠近她一些。
没想到,这句话成为了我说过的话里,最让她心动的一句。
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是,当我们感到自己没有底气的时候,也正意味着我们将要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了呢?
如果是这样的话,你也正在为自己活得特别没有底气而烦恼吗?恭喜你呀,再坚持一下吧,
就一下。
文章来源:我要WhatYouNeed
没有找到相关结果
已邀请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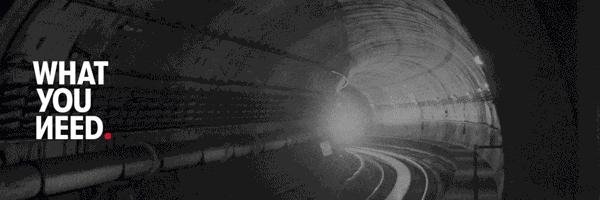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0 个回复